女同小说(女同小说)

在我们的正统文学中,存在同性恋文学吗?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无论是我们温习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书写,还是回忆我们文学启蒙之后的阅读经验,梳理在我的阅读谱系,自然会有所了解。文学并不必然是宣扬道德律令,道德律令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学书写。尤其在我们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文学写作伊始就背上了传教士一样的宿命,每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个道德律令的支撑。在这样早些年还视同性恋为违背天伦与人性,视之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的国度,作为现实的阴影折射的文学书写,自然也会把这一题材深深掩藏在欲言又止的正统文学的背后。
这就更不要说作为同性恋文学的分支:女同文学。从文学的性别而言,或者从女性文学的定义而言,只有女同文学才是纯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按照发明这个文学术语的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的说法,如果真正存在一种女性写作的传统,这个传统最初也是是产生于对男性写作的模仿,而非来自女性在生物学或心理学上的联系。女性写作一直朝着无所不包的女性写实主义方向走去,那是对家庭妇女生活的日常延伸和探索,但万变不离其宗,家庭仍然是家庭,是女性生活写作的重心。从这个意义上,女同文学是正统文学的亚文学,同时也是男性写作的亚文学。在双重的压抑之中,又受限于各种文学他者的逼迫与参照,女同文学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中,自然是彰而不显,默而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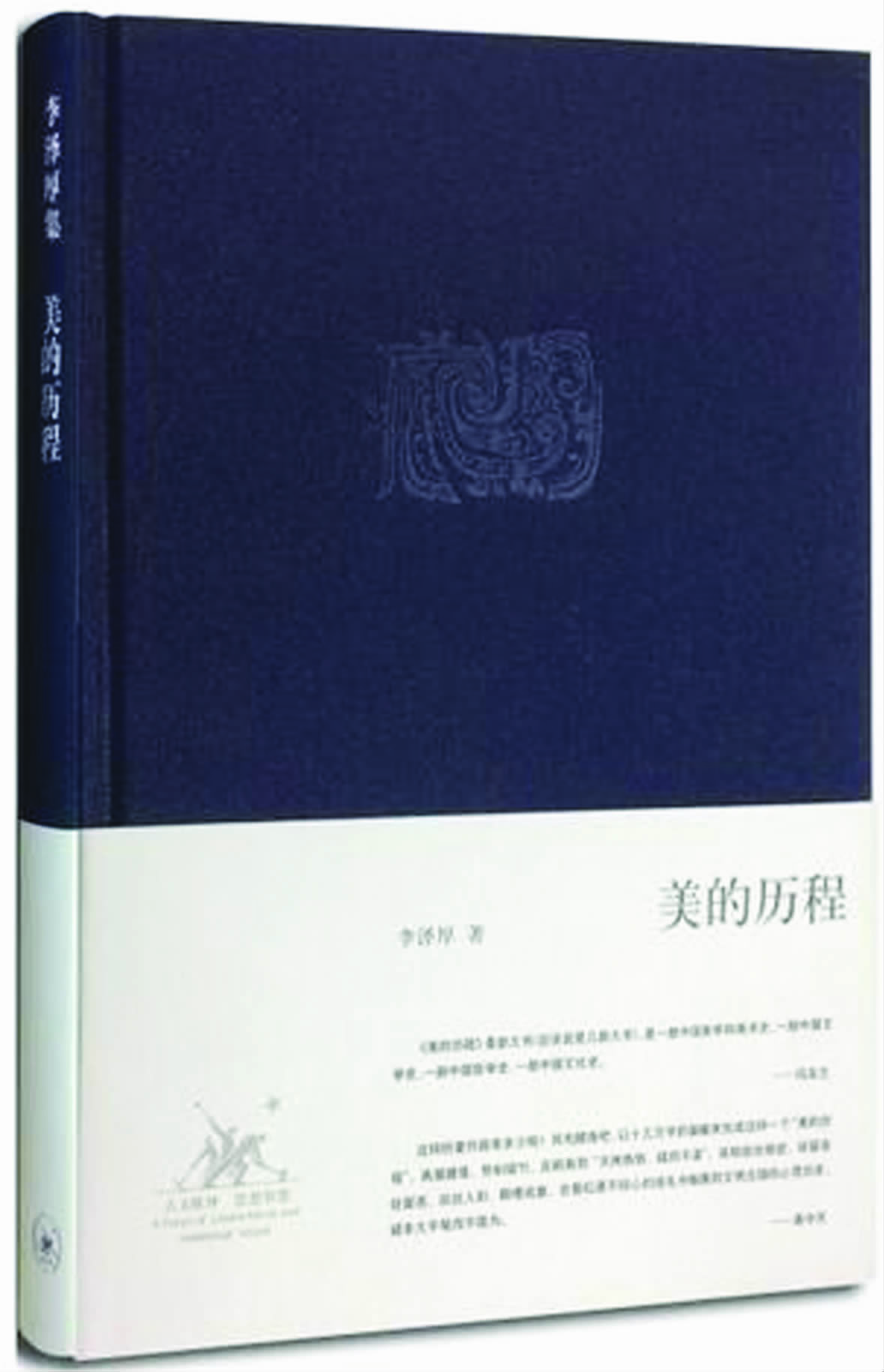
换言之,如何谈论我们的女同文学,无法找到合适而对等的参照点。张爱玲论女人,说来说去还是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两者并无区别。论及女权社会的好处,她就只提到一点: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优秀的女作家并不必然就有女性意识,总会经过时间的淬炼,人生经历的丰富,才会逐渐复苏内心的女性意识。不要说张爱玲,就连苏珊·桑塔格都免不了这种青春期性别意识的困惑,更别说那些被迫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存在“问题”的普通女性。读桑塔格的日记,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在青春期意识到自我同性恋倾向后的自我认同,她甚至已经自觉地用这种身份去解放自己的写作,这种强烈的同性体验让她从焦虑不安中走出来,正视自己的女同身份,开始觉醒和重生,她说:“我想写作的愿望是与我的同性恋有关的。我需要这个身份来当做武器,以对抗社会反对我的武器。”但是令人无比挫败的一点是,就在他意识到自己同性身份的重要性时,她还是嫁给了她的大学老师,熬过了七年的痛苦婚姻。

我用桑塔格的例子对比章诒和今年《邹氏女》中女性人物形象,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但是我需要这种对比,因为在我们的正统文学叙事中,同性恋叙事暗流涌动,却从未现形。尤其是面对更为强大的红色革命叙事,女性主义的弱势形象已经根深蒂固,这种弱势不仅仅表现在女性的性征在革命的狂欢声中被悄无声息地抹去,还表现在女性只能成为男人观看和爱慕的对象,她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取向。所以我不难明白章诒和很直白地打破这种革命话语的禁忌,直接宣称《邹氏女》是写狱中改造的女同性恋的。西方的文学中总有一股激昂的女同叙事,很多女性作家有意识地用这种女同身份的属性作为反抗的方式,她们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觉的性革命,通过身份的归属,寻找同类,梳理概念,归纳情感,异化性别,改写童话,总而言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唤醒自己的性别意识,寻找女性自我的身份认同。

文/思郁
但是相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自觉,中国女性的同性意识大都是被迫觉醒。最为吊诡的是,这种同性意识的觉醒还是在高压政治的呼吁之下,在红色革命叙事的消耗之中,在一个所有男人缺席的环境里,当女人无法从男人那里得到拯救的希望,女人只能依靠女人获得自我拯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章诒和的《邹氏女》凸显出了中国写作语境中女同意识的觉醒。但是也仅仅是最初的觉醒,这种觉醒多少有点不得已为之的意味。所谓情势所迫,与主动觉醒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果单纯从小说的技巧上来看,这本书的结构很差,人物不完整,角色不分明,叙事牵强不连贯,就连小说中张雨荷、苏润葭、姜其丹、黄君树等人物名称都透着一股虚假的琼瑶味道。但是作为一部描写文革改造中女同作品,还是彰显出了章诒和对那段历史的特殊审美需求。前些日子为鲁迅文学奖争吵得厉害,有鲁奖评委针对阿来作品得零票给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你是一个好的虚构小说作家,不见得能写好一部非虚构作品。这个评语反过来说送给章诒和倒是很合适,她能够写好非虚构的回忆散文,不见得能够驾驭好一部虚构的小说。《邹氏女》的很多细节上有历史回忆录的味道,但是她无法将小说人物的设置和角色的分担区分开来,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像一个人,没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所以这部小说唯一的价值在于,她彰显出了一个后革命的禁欲时代里,被压抑的女性群体像。

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这些被红色历史遗忘女囚犯,被革命胜利抛弃的女人们,在一个禁绝的时代环境里,在互相依靠中背叛,在屈辱中苟延残喘,在煎熬中苦苦挣扎。女人的性欲不但没有被这个高压的时代阉割,反而在女人绝望的时候成为了互相支撑的力量。同性意识的觉醒只是为了生存下去,为了在灰色黑暗的岁月里寻找一丝希望的微光。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觉醒看作一个暂时的女性乌托邦,一个幻想的女性共同体。很显然,如果脱离了这个残酷的时代语境,当她们走出监狱,恢复正常生活,也就意味着这个乌托邦的瞬间崩塌。同性意识只能在这种被隔绝的环境中形成,无法形成正常时代的话语力量,开篇张雨荷被释放后的生活描述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好像是很多女性作家的通病,她可以写好一个细节和片段,可以写很多漂亮的句子,但过于自恋的书写限制了她掌控全局的能力,她无法驾驭整部小说的创作。当然,如果能撇开《邹氏女》那些瑕疵不谈,章诒和在细节的营造上,尤其是那些投射自身情感的角色上描述上,还是饱含着深情的笔触。比如小说中张雨荷吃饭的几个章节都写出了一种不动声色的惊骇,大概只有经历过饥荒年代的人才懂得这种荒诞的饥饿感。还有张雨荷去县城购物,突然闻到了迎面女人身上的凡士林的香味,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告别了尘世,结束了灵魂,除了牢狱之苦,更多还是源于她所熟悉生活的死亡,“如美食、如饮茶、与读诗、如听戏,以及少女的对爱情的幻想”。邹开远去世前的一番思索亦是如此,“人生中最残酷的事,根本不是什么青春老去,芳华凋零,而是面对偌大纷繁世界,自己成了赤手空拳的俯首就擒者,其无助无力,与幼儿无异”。
与其说这是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倒不如说寄托了作者自身的情感想象,通过几个女人的故事哀叹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的沦陷,通过女人之间的隐忍与背叛诉说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无力感,大革命的洪流中,没有人可以安然脱身,悄然离去,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是时代的人质。

肖瓦尔特说,如果女性写作的终极目标是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那这屋子就是一座坟墓,就意味着女性退出了政治世界,与男性的权力、逻辑和暴力脱钩。如果女性从她们的独立性中汲取力量,在世界上发挥力量,那么女性文学可以采取任何形式,女同题材自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但是《邹氏女》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女同文学,而是在于它的非文学性弱化了女同文学的叙事。女同文学自然不能仅仅依靠文学史上一两个天才的作品,而是要确立女性文学作为艺术形式的连续性和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邹氏女》的薄弱情有可原。至少它将那种暗流中的文学叙事推演到了舞台之上,从此之后,这种文学会逐渐建立自己的叙事模式,也会逐渐丰富自我的文学技巧,当然,它会逐渐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一间可以向四面开放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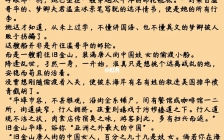


文章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