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临河古镇(长临河古镇开放时间)
与合肥这座城市相遇,总是让人不由得遐想。
诚然,合肥的由来,道听为东淝河、南淝河而成,不知正误,也没寻根究底。仅从字面深入进去,也许并非那么简单。合而肥,合什么,才有肥之果?我们可以谓江河可合,物我可合;那么肥,是所谓指向形体的胖?以当下的生活美学标准,我们不再是以唐朝的“以胖为美”作为标准,早已从个体、肉身走向了开阔和盛大,从物质到精神,从可能到无限,经济肥了,自然肥了,人文肥了。这个深秋,有幸在合肥这座城市里走一走,雅集纵然短暂,只觉得自己也“肥”了。

比如瓦松。这是我在长临河古镇发现的,准确地说是《雨花》副主编育邦先发现的。我们并排走在“青砖小瓦马头墙,木雕门窗冬瓜梁”的街巷里,徜徉的状态,就像呼吸,进入一种自然的状态。我以为,对古镇的解读,最好的方法是让肉身融入其中,身心随着街道起伏的灰砖路面,信马由缰似的,这种松散,也许才能抵达古镇的纤毫之处。转身回眸之际,我们被一处低矮、灰瓦屋脊的民居所吸引,鱼鳞片的瓦沿上,密集整齐的瓦松,平铺在上面,整齐划一的景象,让人惊诧,似乎自然之手抚摸过似的,没有留下一点空白,实属罕见。我们又向旁边的屋顶望了望,瓦松也有,稀疏可见。疑惑来了,是人为的,还是风中落生的?屋是老屋,锁已生锈,主人不知去向,或许一直空着,无人知晓。只有瓦松寂寞地在屋顶生长,迎着日头,顶着风雨。在城市钢筋水泥森林的逼迫下,一寸寸生长,把古意镶嵌在瓦缝间。我们多看了会瓦松,一时间有点恍惚,青砖灰瓦建构的古镇,把“古”字点睛的,是屋顶上的瓦松们。要实现这片密集的瓦松,没有时间的悠长、与瓦片的契约,岂能如此繁盛?
我们继续游荡在街巷里,扑面而来的,有百年邮局、吴氏旧居等建筑,斑驳的墙壁与黯淡的光线,深邃了更多的古意,可那片瓦松早已挤满了心室,于是抬脚匆匆而过。

到了湿地森林,由瓦松带来的欣喜不断扩大、漫漶,这完全是屋顶上瓦松的放大版。瓦片换成了湿地,不足三寸之高的瓦松已被入云参天的松树、杨树等替代。森林的出现,它比瓦松来得更加辽阔、丰盈。它把古镇的古,蔓延为无尽的林海。电瓶车在其间行驶了好久,依旧没有看到尽头。林间人工居所店铺寥寥,游客也稀少,或许是季节的缘故。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森林浩荡的原因,人与树木在空间的争夺上,能够侥幸地胜利一次,我以为合肥滨湖湿地做到了。随着眼前密集的树木铺满眼睛,还有林间叶落的静寂,偶尔飞过的鸟影,加速我们逃离湿地森林。森林里待久了,被树木感染了,再入喧嚣的都市会产生不适感,毕竟人不同于树,背负着太多的欲望和沟壑。
从长临河古镇到森林湿地公园,忽然脑中翻阅起中间还去了巢湖。作为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方圆八百里,坐在游船上,烟波浩渺、苍茫辽阔等词汇一下子翻卷过来。这种汇聚,也包含巢湖与合肥的相会,历史上巢湖与合肥也多次合合分分。作为出生于洪泽湖畔的人,在被巢湖里一座博爱的姥山岛感慨唏嘘之后,心思沉浸在长临河古镇、森林湿地中。如果以巢湖为中心,长临河古镇在东,森林湿地公园在北,换而言之,从自然景物到人间烟火,隐秘的是巢湖的水泽天光。镇以河居,森林傍水而生,内部不正是暗藏着这个偌大的湖泊?逐水而居,这正是人类几千年来繁衍生息的密码。
“合肥”二字再次跳到面前。有人解析论道,合者,兼并天下;肥者,海纳百川。如此,不免想到唐玄宗与韩休之事。宦官因看到皇帝为韩休屡屡劝谏争辩而愁眉不展,遂有劝皇帝罢免韩休之职,而得之欢乐,遭到拒绝。唐玄宗揽镜而言,“吾虽瘠天下肥矣”。就眼前景而言,肥之天下,源之于水,水生万物。
一个“肥”字,正是我这两天来游览合肥之景的感悟。人间烟火、都市霓虹之外,合肥人在自己的天下里,深得“肥”字的精妙,只有顺其自然,懂得自然之道,方能得乎天下。
刘铭传故居,让“肥”字更多了几分意蕴。肥西大潜山,这是刘铭传故居所在地。念及台湾首任巡抚、肥西人氏刘铭传,我们自然想起1884年一场血与火的中法之战,想到海峡对面的宝岛台湾。布衣出身的刘铭传,饱读经典,“静研中外得失”,常与心怀忧患的高蹈之士结交。这也是后来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他挺身而出,肩负起抗法保台重任的缘故。
晚年的刘铭传身在肥西,却思肥天下。令人悲哀的是,刘铭传抚台六年,最终因清朝分崩离析,而至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台湾被割让,后吐血而亡。这是分的悲哀。

夜宴罍街,忽闻有黄梅戏之听,不甚喜之,后因天色太晚而取消,不过,留在内心也许更会丰盈。作为淮河两岸之人,黄梅戏日久聆之,早已谙熟于心。即使山民樵夫,提起《天仙配》,也能吟唱几句。这是合肥的声音,也是天下肥的声音。
幸哉,合肥之行,与众师友同行,见微友洪放,遇冬林师姐,还有红莉、玉兰、中银等诸君,自己不免也肥了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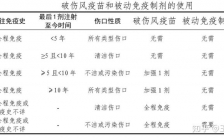

文章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