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边的老人(桥老人的精神品质)

小时候的偶像特别多,关于作家有两个,一个是《小王子》的作者,虽然我当时一直记不住他的名字,但是他会开飞机,我觉得会开飞机的作家特别了不起,所以崇拜他。
另一个作家偶像是海明威,那是小学五年级的一个晚上,我吃完饭抱起足球要下楼,妈妈喊了一句“刚吃完饭不许运动”,于是爸爸强迫我坐下来听他读了一篇小说,小说叫做《桥边的老人》,是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里的作品。听完那篇小说我郁闷了好久,一种莫名的哀伤盘踞在我胸口,我开始认真地读那套两卷本的全集,海明威的小说带我走进一个新的世界,和狄更斯、高尔基等作家不同,他的短篇小说里充满了失败,但是那些失败衬托出的是永不服输的精神。
小学毕业的暑假我被检查出了眼底疾病,医生说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又叫做视网膜退化症,视网膜中的细胞停止了更新,当现有的感光细胞衰亡,我就失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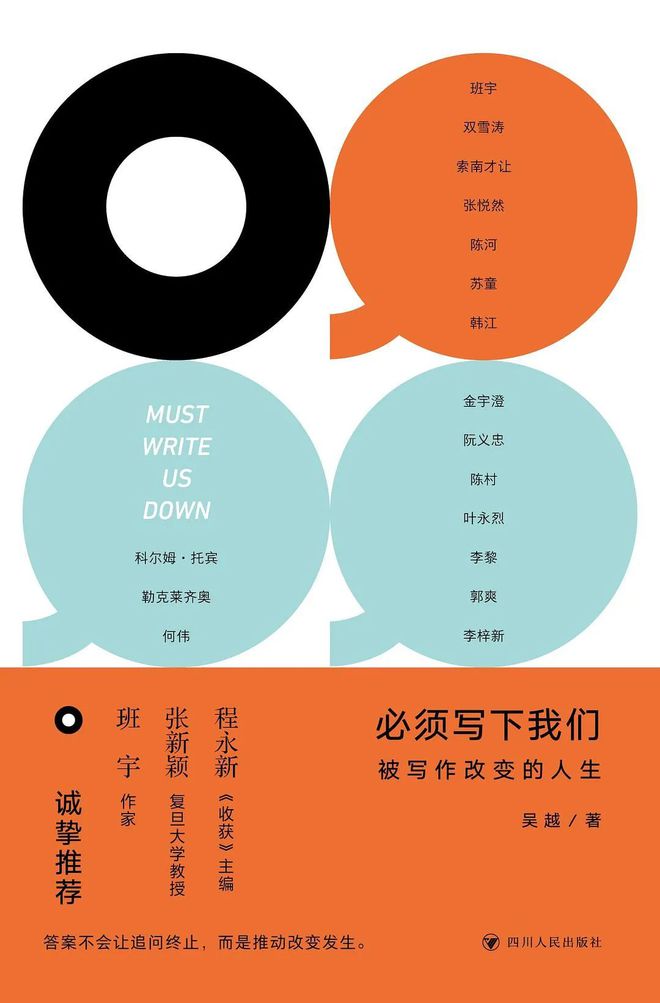
在北京跑了几个大医院,都说不能治,301医院的一个医生特意留我父母深聊,他要我回避,但是我躲在科室门口偷听,其实他所说的坏消息我在其他医院都听过,唯一没听过的是他说出了年限,他说我的眼睛还能再用十到二十年,能不能用到二十年取决于有没有保护好,视疲劳是我眼睛的杀手,所以我不能看电视,也要少看书。
我把医生的叮嘱告诉班主任,所以初中三年我的家庭作业可写可不写,但是我并没有真的让自己的眼睛休息,我开始疯狂地读书,我买来许多哲学著作,我要寻找命运的答案。
青春期是身体发育的阶段,视网膜的退化进程也在加快,我的视力在明显地下降,视野在明显地缩小,我终于还是想到了放弃,因为我有了一个发现——失明了,一切都是白搭。
放弃之后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小说是一直在读的,连上课的时候也在读,因为它是我唯一的消遣,有一天我在书店看见了海明威的名字,这位我曾经的偶像,于是我买了那本《老人与海》,万万没想到,我苦苦追寻的答案就在这本小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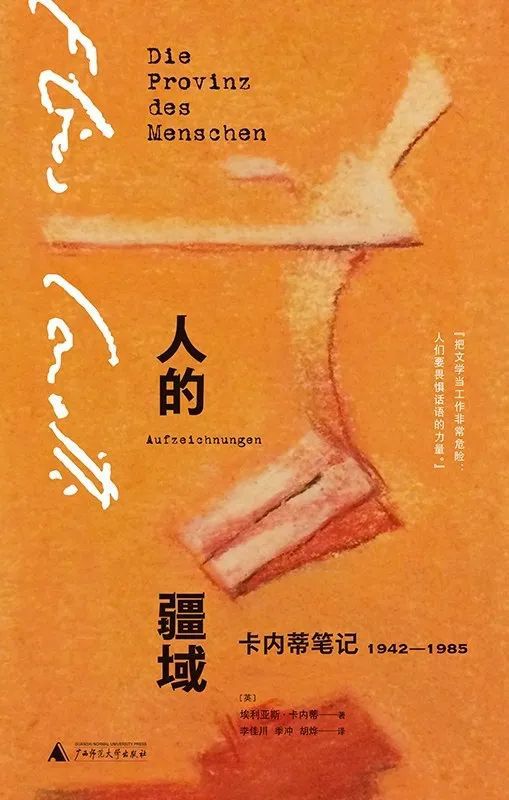
小说中的老人好不容易打到一条大鱼,但是那鱼太大不能拉到小船上,只能在水里拖着,鲨鱼闻着血腥味拥来,老人和它们搏斗着,可是上岸之后,那条大鱼还是只剩下了骨头。
那么老人是成功还是失败?海明威的答案是人可以被打倒,但是不能被打败,我在小说里看见了自己,没错,我的结果是失明,就像那条大鱼的结果是白骨,就像每个人的结果也是骨灰,如果总是盯着结果,那当然什么都没有意义。但是人活着是为了这个过程,当我想到这些,我重新振作了起来,转变思维之后我明白一个道理,恰恰因为我会失明,我更应该在失明之前好好努力,让这个过程更加充实。
是小说帮助了我,是小说拯救了我,我为之前一直把小说当消遣感到遗憾,原来小说有很多种,确实大多数小说是娱乐性的,但是还有一些小说做出了深入的思考,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时我惊呆了,仿佛一面魔镜照出我的灵魂,我彻底爱上了这样的小说,那时候是初中毕业的暑假,我决定要写小说。
我带着一书包的小说去外地读盲人学校,父母希望我考上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但是我很明显把时间都花在小说上,高中几年我写了很多短篇小说,不停投稿,后来发现只有一篇《寂寞公路》值得保留,但是那篇小说也要在几年之后才在《福建文学》发表,完全拿不出成绩的我让父母十分担忧,即将读高三的暑假,父亲带我去见了一个诗人。

诗人陈道辉是我们县当时唯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住在农村,他认为,我还是应该上大学。从陈老师家出来,我就开始流泪,我认清了一个现实,考上大学我就可以获得五年的校园生活,也就是我还可以专心地写作五年。
高三我彻底收起文学,为了争取到五年的文学时间,我没日没夜地读着教材做着题海,被大学录取后父亲又带我去见了陈老师。这一次,陈老师说,要坚持自己的理想,要追求高品质的文学,只要文学上有所收获,生活上的任何困难都不算什么。
上大学后我开始尝试写作长篇小说,把电脑文档里的字体调成最大的初号,每天晚上在宿舍里敲键盘,但是我的写作素材明显不足,每次开篇写到四万字就不知道还能写什么,集体宿舍也不是一个适合创作的场所,常常有同学凑到电脑桌边问我在干什么。每当这种时候,我竟然没有勇气说我在写小说,我担心自己会被传说成一个怪人。
失败了四部长篇,我决定先放一放,我的专业针灸推拿学属于中医,于是我开始在专业学习的同时为小说积累素材,准备今后写一部关于中医的小说。这下学习成绩立刻提上去了,那些需要重修的课程全部通过,考试不再挂科,大学毕业之前有几个月时间用来准备论文,我把毕业论文写好后,剩下的时间属于小说。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逼入绝境才能激发出潜能,我在家里没日没夜地写,连做梦都是小说里的情景,写作异常顺利,文稿写出三分之一的时候,整部小说已经基本在我的脑中完成,我需要做的只是将剩下的部分打出,每天起床都有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我坐到电脑前,到最后阶段,我的眼睛已经支撑不住,视疲劳让我眼前的世界不断变色,电脑上的大字体已经揉成一团,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打字,只是打出许多错别字,后来好在父亲帮我校对。
我用了整整五十天的时间打出了长篇小说《星期八》,让眼睛好好休息了几天,可是视力不仅没有恢复,甚至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早有心理准备,医生的预测很准,没错,十年到了,我根本没想过保护眼睛,所以只用到十年。
小说的修改和写作同样重要,我给电脑安装上读屏软件,它可以把屏幕上的字读给我听,又修改了几个月,《星期八》正好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出版了,这部小说得到许多好评,居然开始有人把我称为作家,让我有了可以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乔伊斯说“在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里,失明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件”,博尔赫斯觉得乔伊斯有点夸张了,他说失明确实很不好,但是一个人只要选择了写作,所有的坏事都可以当成宝贵的经历。乔伊斯和博尔赫斯都是我的榜样,我比他们幸运得多,他们失明以后只能通过口述来创作,而我借助电脑里的读屏软件就可以用普通的键盘写作,音箱会念出我打的每一个字,我也不需要别人读书给我听,借助扫描仪我可以把书本制作成方便听读的电子书,我与文学之间基本上是无障碍的。

文字是一个个光量子,当它们排列成文学就可以把世界照亮,我还没有写出心目中最完美的小说,对文学的追求让我忘记失明的苦恼,我的幸福感很容易获得——把我深爱的某部小说重读一遍,读到一篇好作品,自己写出一个好句子。
命运考验过我,文学救了我,我相信,我深爱的文学一定也爱我,它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它也一定会陪我走到最后。
吴可彦
1990年生,出版有长篇小说《星期八》《茶生》,短篇小说集《八度空间》,漳州市盲人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阅读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文章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