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楞柱(希楞柱)
图书荐读
闪光的河 流逝的河
豆瓣·姜将将
对于阅读者来说,迟子建是一个令人放心的作家,也就是说,她不会让你失望。
我读《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初的原因是它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授奖辞中说它,“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当然,并不是获奖的书就值得购买,对另外三本书我就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达不到我的阅读要求。
我从一个阳光照耀的初春的上午开始阅读此书,几乎是手不释卷,在第二天读完了“清晨”和“正午”两个部分。我得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在阅读中我有了基于文学本身的久违的沉浸。即使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也不得不由衷发出赞叹。
作品以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口吻,叙述一个民族的生存、坚守和文化变迁。“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它的第一个句子。这些比喻的、完成式的、叹息着的句子,有一种来自命运本身的苍茫意味,简约、直接,使忧伤与诗意洋溢而出,为整部作品确定了基调。

这部作品有着强烈的“唯心”色彩,大自然中的树木、野兽、河流、天空、星月,有着和人一样的灵性,或者说是神性,这使它超脱出我们当下的尘世经验,显现出清新、原始的格调。奇怪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它常常引发我类似怀乡的忧愁——我会忽然想念已经远逝的葱茏岁月、想念少年时代的田野、某个初春曾经去过的山林,想念起初恋或者倾心夜谈的朋友。
有多个评论说,这部作品是一个民族的史诗性挽歌,如果以一个读者看,这首挽歌并不单单是哪个民族的挽歌,抑或还可以说是一曲关于某种美好生活的挽歌、关于人类某种价值观和生命方式的挽歌。人们仰望天空,沉醉河流和山林,心中敬畏神明,唱着单纯的歌曲,生于“风声”,最后又被埋葬于风中。作品中除了作为主要人物的形象之外,更为动人的是变化的白云、闪烁的星光、能望见天空的希楞柱、驯鹿、月亮、萨满的舞蹈、桦树与松树、明亮的流水,它们既是人物的生活背景和依据,也同样是书中的主角。它们共同构了这个世界美好而又脆弱、欢乐与苦难交织、幸福中满含悲伤的生命景象。
作为一个小说家,迟子建从来就不以塑造人物、讲故事、设计冲突和结构见长,而是以优美的语言、从容的节奏、丰富的意象取胜,她所做的不是描绘具体事物,而是倾述,从内心向世界的倾述。事物经过心灵的含蕴之后,再表达出来,那些文字就被赋予了精神意义。语言因此产生了内在的节奏和张力。品读一下某些段落,它们几乎可以咏唱,即使并不押韵,却有一种明显的音乐性。
我以为,中文之美包括了多个层面,每个字词在它有本来意义之外,还有着独特的形状,独特的色彩,独特的声响,甚至还有独特的味道和触感。从事写作的人,如果反复推敲过一万个以上的好句子,最好是你曾经有较长的诗歌写作经验,就一定会对文字的形状、色彩、明暗、声音和气味有所领会。
迟子建这部作品中的语言,可能是她作品中最好的语言(我能不能说也可能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好的语言?),比喻丰富,感情充沛,色彩绚烂,节奏感极强,就像那条闪光的额尔古纳河,丰盈、宽阔,伴随着风的歌吟,在夏日山谷中汤汤流动。当然,它述说的是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故事,关于美与哀伤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出现和消逝的故事。

(注:文章有删减)
原文欣赏
额尔古纳河右岸
清晨(节选)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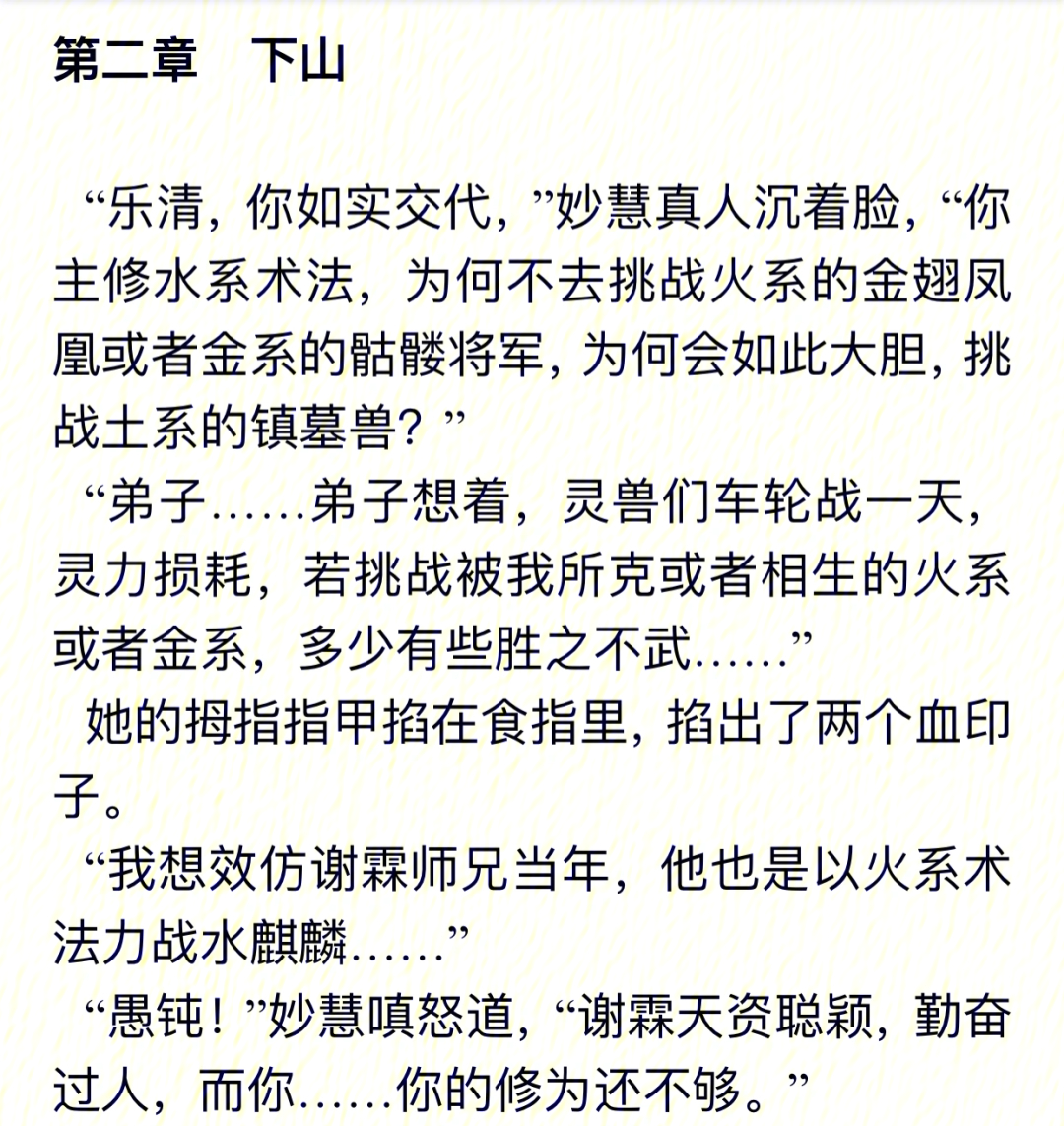
西班他们刚走,雨就来了。在这之前,连续半个多月,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了。我不怕天旱,但我怕玛克辛姆的哭声。柳莎到了月圆的日子会哭泣,而玛克辛姆呢,他一看到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就会蒙面大哭。好像那裂缝是毒蛇,会要了他的命。可我不怕这样的裂缝,在我眼中它们就是大地的闪电。
安草儿在雨中打扫营地。
我问安草儿,布苏是不是个缺雨的地方,西班下山还得带着雨?安草儿直了直腰,伸出舌头舔了舔雨滴,冲我笑了。他一笑,眼角和脸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眼角笑出的是菊花纹,脸颊笑出的是葵花纹。雨水洒下来,他那如花的皱纹就像是含着露珠。
我们这个乌力楞只剩下我和安草儿了,其他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以往我们也下山,早些年去乌启罗夫,近年来到激流乡,用鹿茸和皮张换来酒、盐、肥皂、糖和茶什么的,然后再回到山上。但这次他们下山却是彻底离开大山了。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布苏,帕日格告诉我,布苏是个大城镇,靠着山,山下建了很多白墙红顶的房子,那就是他们定居的住所。山脚下还有一排鹿圈,用铁丝网拦起,驯鹿从此将被圈养起来。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两年前,达吉亚娜召集乌力楞的人,让大家对下山做出表决。她发给每人一块白色的裁成方形的桦树皮,同意的就把它放到妮浩遗留下来的神鼓上。神鼓很快就被桦树皮覆盖了,好像老天对着它下了场鹅毛大雪。我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不过我不像其他人一样走向神鼓,而是火塘,我把桦树皮投到那里了。它很快就在金色的燃烧中化为灰烬。我走出希楞柱的时候,听见了达吉亚娜的哭声。
我以为西班会把桦树皮吃掉,他从小就喜欢啃树皮吃,离不开森林的,可他最终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把它放在神鼓上了。我觉得西班放在神鼓上的,是他的粮食。他就带着这么一点儿粮食走,迟早要饿死的。我想西班一定是为了可怜的拉吉米才同意下山的。
安草儿也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但他的举动说明不了什么。谁都知道,他不明白大家在让他做什么事情。他只是想早点把桦树皮打发掉,好出去做他的活计。安草儿喜欢干活,那天有一只驯鹿的眼睛被黄蜂蜇肿了,他正给它敷草药,达吉亚娜唤他去投票。安草儿进了希楞柱,见玛克辛姆和索长林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他便也那么做了。那时,他的心里只有驯鹿的那只眼睛。安草儿不像别人那样把桦树皮恭恭敬敬地摆在神鼓上,而是在走出希楞柱时,顺手撒开,就好像一只飞翔的鸟,不经意间遗落下的一片羽毛。
虽然营地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
我回到希楞柱,坐在狍皮褥子上,守着火塘喝茶。

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了。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但他们告诉我,布苏的每座房子里都有火,再也不需要火种了。可我想,布苏的火不是在森林中用火镰对着石头打磨出来的,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让人的心和眼晴明亮呢?我守着的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我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达吉亚娜走了,西班走了,柳莎和玛克辛姆也走了,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安草儿自己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说话。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我知道这对冤家跟人一样,也长着耳朵呢。
END
编 辑 | 王书嫣
初 审 | 郑美林
复 审 | 张 兰
终 审 | 毛雅琴







文章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