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雨(毛雨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重建我的家乡”,毛晨雨一字一句地说,脸上难掩羞怯,声调里却满是自豪,轻易穿透连锁咖啡馆里刺耳的碾磨声。
采访毛晨雨的前一天,他的新片《拥有》刚刚举办了小规模的放映。他的生涩风格在影像中一脉相承,基层农民访谈的文本通过符号和观念重构,带入强烈的主体意识,区隔了它与以往“作壁上观”式的纪录片范式截然不同的立场。
文化人王小鲁评价,毛晨雨是中国纪录片导演中难能可贵的具有思辨能力的人,其对纪录片的探索超越了纪实主义的美学内在。在洞庭湖畔隐居的近十年里,毛晨雨不只是单纯地拍电影,他将自己的影像记录与乡村社会观察以及乡村文化重构联系在一起。
2004年,当村里读书最好的“大学生”带着浓烈的乡愁返回时,他发现精神上的故乡已无路可寻。乡村文化仪轨中最为根系的土地信仰,在涌向城市的大军面前崩塌。“一个再小的村庄也无法从潮流中割裂出来”,他叹息诗性乡村的终结,却没有逃离,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乡村文化的重建实践。
他租下乡亲的田地,在那里耕种出一方生产安全、环境健康、生活永续、经济可观、民主启蒙的小型社会范本。
回乡种田
湖南省岳阳县松源镇的细毛家是一处仅十来户人家、三十来人口的自然村落。从镇上走到毛晨雨家老宅的几公里路途上很少看见行人,和中国大部分乡村情境相似,这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留下老年人偶尔走在田地间背着手缓缓而行。
去年2月,毛晨雨承包了20亩土地,搞起了一个生态主义农场的实验,将其命名为“小生态之肺”。父亲的看法是,他终于干了点实事;母亲则表现出不安,“哪个种田的发了财?我不要他种田”。
毛晨雨和他二姐一度是这个村的骄傲,在他二姐考上当时的中南工业大学之前,这个村没出过大学生,而毛晨雨又继二姐之后,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作为家里最小且是唯一的儿子,他说,自己是在“娇惯”中长大的,不善劳作,弯腰插秧都会感到眩晕。在儿时的记忆中,“秧苗被插在村庄的每个小角落里”,昂着头宣示土地的精贵。而如今的细毛家屋场,近五百亩稻田只有不到1%的稻田种了早稻。
“土地的神性彻底瓦解了”,毛晨雨有些悲观。在回到细毛家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镜头都在勾勒村民口中渐行渐远的神灵形象,土地神、窑神已无人问津,与生产有关的祭祀仪轨几乎废弃。毛晨雨回到故乡后拍摄的第一部民俗志纪录片——《细毛家甲申阴阳界》直视了这一信仰危机:村里引入了六合彩,村民肆无忌惮地讨论如何买码、中大奖迅速致富,话题不再与农耕关联。神圣的扶乩降神被当作获利手段,神灵屡测六合彩不中后,遂遭乡人怠慢。《拥有》的调查呈现则更赤裸,结盟和权力寻租支配着乡村的话语空间,“土地和耕种”沦为伪命题。
信仰崩裂的后果是约束不再:高毒性的农药被广泛采用,“农药喷洒之后,土壤中的生物基本都要灭绝,周边生态里连青蛙都没有”,毛晨雨说,人们对土地一味地索取,不再愿意投入。“这其实不是农民小农意识的变化,是凸显了一种与社会运动相适应的跳动的东西。”他感到这个社会很现实,越来越快地要奔向某个目标,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在毛晨雨租佃的这片农场上,他企图恢复一种传统的劳作方式,精耕细作,低效但生态。带点赌气的意味,他选择的是一种在湖南几乎被淘汰掉,没有生存能力的“洞庭红?”。此品种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是本地主流稻种,后来逐渐被高产稳产的杂交稻、超级稻及农户私自种植的转基因稻所取代。
农场完全采用人工作业的方式除害,肥料用的是“油菜枯”,白酒、白醋、食盐、“茶枯水”则作用于杀菌灭虫。“茶枯水杀菌,这是以前就有的经验,但是成本比较高。粮食不足催生了化肥农药的使用,如何提高产量成了核心问题,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认为茶枯有价值了。”整整一年,他奔走于各个村庄,“推销”自己的生态农业概念,亲戚被拉过来帮忙种地,“欠了20多个人情”,他说。
有更多农耕经验的父亲则是农场的管理者。起初,他担心周边的农田都打农药,虫子会被赶到自家的稻田来。结果证实,这块地的发病率反而是全村最低的。
与此同时,一部命名为《生产传统》的纪录片在“二月二龙抬头”这天开机,记录农场的全部生产环节。毛晨雨的夫人是位画家,她正在画一本现代版的《天工开物》,展示耕作经验和传统乡土文化。

农场去年的种植效果不错,获得了大丰收。毛晨雨在淘宝上开了个名为“稻电影农场”的小店,在考虑到成本收益比之后,4000g的精米礼盒标出了398元的高价,每斤则卖到了66元。“我做的事情首先是让大家认识到土地还是有价值的”,他说。
“稻电影”
毛晨雨的离乡和返乡都曾引起过轰动。1996年,他被风光地送出村庄。2004年,当他拿着摄像机回乡时,大部分的村民都认为他“落难了”。
城乡二元的制度设计由来已久,村民也否定了自己的家乡,抛弃土地,涌入城镇。毛晨雨却带着乡愁返回故里,“现在依然保留了农村户口”。
毕业后的毛晨雨从事完全与专业无关的工作——他短暂地为北京电视台《纪录》栏目拍片,之后组建了电影工作室。2003年秋,他进入湖北神农架,开始了纪录片《灵山》的拍摄。彼时,关于神农架地区发掘到史诗《黑暗传》的消息不胫而走。毛晨雨独自拎一台机器在一个村庄拍摄,希望做一些语言史的社会调研工作。“非常选题导向的”,在后期制作时,他开始反思这种将逻辑施加在拍摄对象身上的在地调查。
“我为何不做自己熟悉的文化”,他想。次年,毛晨雨回到湖南,开始拍摄稻民和稻田文化相关的“稻电影”。他绝不是在单纯地拍电影,而是将拍电影和社会观察与乡村修复联系在了一起。
此间的乡间已经不是记忆中那么美好。“你记得80年代西瓜很好吃,远方是哪里的追问很诗意,现在却只能感觉到乡村被一个体系、一个潮流卷着走,一个再细小的村庄也无法割裂出来。”故乡的陌生感反而增添了无限的乡愁,“因为这已不是放弃故乡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接下来的几年,尽管毛晨雨也在上海结婚、安家,但他仍然上海、湖南往返跑,将自身全部之生产系重在了乡间。

“这里能不能保持一种干净的生产,一种自律的形式,一种民主多元的可能空间,同时也有一点风花雪月的事情呢?”他反复思索。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介入,他的影像就不仅仅满足于纪录表象本身了。在研究农村秘密信仰的《神衍像》中,“主角”是摇曳稻浪的半条船,颇有些装置艺术的意味,正是毛晨雨创作并植入的“文本”。
《神衍像》解决了这条船的来龙去脉:毛晨雨的祖父和父亲是当地的傩师,侍奉的神明是杨泗将军菩萨,相传是杨家将中的杨四郎。父亲扶乩时,有时候写成“四”,有时候写为“泗”。2007年洞庭湖君山岛游览,毛晨雨看到了当年钟相、杨幺起义的集结钟,发现杨幺在义军领袖中排行第四,被时人称为杨四。起义失败后,杨幺跳湖自杀未遂后遭杀害,由于跳湖不死,人们认为杨四是水神,于是在四前加了三点水。那条船就是杨幺跳湖时的座驾。毛晨雨认为民间非常聪明,因为不准祭祀叛将,所以就把名字混淆起来,得到祭祀的合法性。
“稻电影农场”组织的定期影片放映也遭遇到某种认同上的阻碍。毛晨雨至今已经生产出10部纪录片,但乡亲不感兴趣,“除非是看几年前拍的片子,比如2008年看2004年拍的,他们会觉得上镜的人很好玩。”
“新乡绅”
去年,毛晨雨开始雇人扩建老宅,那是一座门厅开放的仿古建筑,仿照当地曾出现过的最为豪华的乡绅大宅而建,在迎面一片稻浪中十分扎眼。没有买车的毛晨雨希望通过盖房子这件事释放一种经济能量,“这是世俗观念的植入,是一种在当地获得话语认同的必要路径”。
摄影机和大学生身份曾为毛晨雨带来过话语权。村民一方面认为这孩子落难了,一方面又认为他曾在电视台工作,仍连接着某种通往权力的通道。“如果我不是大学生,大家肯定认为我疯了”,他也如此自嘲。

老宅通敞明亮的大厅兼具功能性,那是麋鹿学社的所在地,乃毛晨雨新近设立的一个乡村书院,“是个谈话的地方”,他定义。艺术介入的手段成效甚微,让他思考另外一种文化建设的可能性。
书院里摆上一些从上海带回的物件,他沏一壶普洱茶,邀上门者对饮,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从“农业还有希望吗?”到“化学怎么学?”,有时可以聊到半夜12点。上海电影圈的朋友们偶尔也加入到这场“启蒙运动”中,“去年的聚会时,老师就分散居住到村民家中,有一种知青下乡的感觉,”毛晨雨认为,这至少会令乡民感觉到他们的生活也是可以向外扩展的。
在毛晨雨的眼中,他正是在扮演一个新型乡绅的角色,通过自己的投入和维系,一点点激发周遭的活力。“我回到那个村庄,它确实活了”,他并不掩饰一丝得意。有人告诉他,因为毛家大宅总是亮着灯,自己竟不怕鬼了。留守村庄的老人有了交谈的对象,他为他们拍照,也拍摄他们。今年春节,就在麋鹿学社的闲聊中,11位在外上学打工的年轻人表示农村有机会,自己愿意回来,“我回去后生产出了一些东西”,他有些激动。
有了麋鹿学社的基础,毛晨雨打算筹办更为固定的乡村聚会,主导一些关乎生态农业的话题,比如“种马铃薯是否合适”、“不打农药”等,这些无意识的个人经验交织在他看来非常重要,可能会在村内构成新的公关空间。“它很有可能将青壮年凝聚在一个体系内谈话,他们中有人的父亲就是村领导”。
修复乡村习俗的努力也正在进行中。他准备组织30位村民在“二月二”这天抬着菩萨游村,祈祷减少瘟疫丰产丰收、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等。“仪式承载了文化,能不能先从形式上重建它呢?”他想。
乡村实验
今年早些时候,从附近陈氏村落来了位在外发展的中年人,想从毛晨雨这儿买100斤“洞庭红?”送给长沙的朋友。送上门的生意,毛晨雨却拒绝了,建议他买两头土猪送人,那实在得多,不仅如此,他送他一礼品袋红米品尝。
在毛晨雨和夫人经营的“稻电影农场”淘宝店中,“洞庭红?”的销售并不畅通。“我没法做商人”,他有些气馁,一旦人家问他什么,表现出对“稻电影”的支持,他就再不好意思做买卖,干脆送人。“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他自知。
对于农场的经营,毛晨雨有一系列的蓝图,至少听上去是可行的。一是通过生态种植,增加每亩地的产值。二是将那些剩余的陈米,于每年7月之后酿成酒,一方面利于保存,一方面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经济收益绝不是他的唯一考量。在毛晨雨的设想中,稻电影农场这样的平台是可以生产出完整的经济文化系统的。他演绎他的逻辑:农业生态一旦增加了土地的价值,一个因为经济绩效而联系起来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就可能被建构。如果生态田扩充到100亩,那么这个经济主体就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足以确保整个村庄的价值模式是生态和平等的。“我其实想在这中间种出民主(民智),种出人的意识来”,毛晨雨说,这是一种通过经济方式主导话语空间的途径。
对于记者“这个系统的关键是商品的流通”的提醒,他似乎不太在意,“这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又没有时间考虑,又得去想电影了”。
这个系统目前遇到的麻烦是毛晨雨只能自己承担成本。当他开始租种稻田时,尽管乡邻认为150元一亩地的租金已经够了,但他坚持支付500元一亩,“这是非理性的经济行为,理性的行为是如何把150元的租金压缩到140元”,他头脑清晰,却丝毫不在乎,“我就是想通过经济方式提高人们对土地价值的认识。”
“不计成本”贯穿了毛晨雨乡村重建实践。这几年,他一直宣扬构造无公害生态园的重要性,他是个行动派,干脆自己掏钱为村民购买无磷洗衣粉,试图从上游控制村庄的污染排放源。
事实上,毛晨雨的经济境况并不如“乡间豪宅”彰显得那般气派。他坦言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都过得十分窘迫。拍摄独立纪录片几乎不能为他带来任何收益,而稻电影农场的建设却投入不菲,导致他目前至少背负了超过7位数的债务。
“这是乌托邦的方式”,他并不否认自己的努力是基于一个特殊样本的乡村实验,输血性的投入继而可能演变为维持性的投入,并不具有可复制性。“乌托邦需要有人牺牲,只要牺牲能够种出适宜的生产模式”,他目光倒是坚定。他的下一个计划是把村里的500亩稻田都改造成不再依赖化肥农药,依然可以生存的生态。那时,农民每亩地的租佃价格可以被提高到1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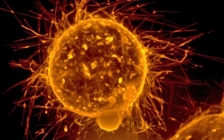





文章评论(0)